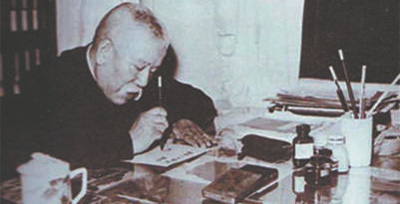
谢觉哉(1884-1971),宁乡人,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部长、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务。
□孙意谋
1941年7月4日,“延安五老”之一的谢觉哉,在日记中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
偶想到应蕙兰同志,意其死久矣,不会变节,几年无从获得消息,在洪湖作俘时有念她的诗,久忘记了。一九三四年在江西有忆她的一首词《望江南》,录于此,以当纪念。
人去也,几度草萋萋。形影已随湖水逝,梦魂不共岭梅归,生死别犹疑。
愁无奈,旧事怕重提,鼓枻菱湖晴荡漾,露营禾垅日清凄,情景尚依稀。
这是谢老对洪湖女烈士应蕙兰的深情回忆。
“人去也,几度草萋萋”,八个字破空而来,悲凉寂寥、哀沉凄惋,字中含情,句间有泪,表达了作者对应蕙兰被俘后的思念,她到底是活着,还是已经英勇就义?“形影已随湖水逝,梦魂不共岭梅归,生死别犹疑”三句,进一层描写对应蕙兰的别绪离愁,她的身影像洪湖水一样流去了,相信她已光荣牺牲,但为什么她英雄的魂魄不一起像江西大庾岭上(1934年谢老在江西)的红梅一同来到我的梦乡呢?“生死别犹疑”,再现了作者思念革命战友生死未明的复杂微妙的心理情绪,知道她已经没有生还的希望,于是才把她比作傲霜斗雪的红梅,崇敬和赞誉之情蕴含其中,溢于言外。
“愁无奈,旧事怕重提”,既是深切悼念的继续,又是进入深情回忆的过渡。人们经常有这样的情况,越是怕想到的事,越是不由自主的袭上心头,难以排解。“鼓枻菱湖晴荡漾,露营禾垅月清凄,情景尚依稀”,概括描写他们在洪湖上日日夜夜的战斗和生活,其中有风和日丽、划船采菱劳动的幸福,也有寒夜在田野宿营战斗的艰苦。以“情景尚依稀”作结,含蓄隽永,余味无穷。
谢老是怎样认识应蕙兰的呢?这还要从1931年说起。
1931年秋,由于顾顺章叛变革命,上海的党组织受到严重破坏,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者被捕。此时身在上海的谢觉哉,只好转移到湘鄂西革命根据地。
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地处湘鄂两省西部边界,山岳连绵,湖港交岔。南昌起义失败后,贺龙、周逸群等利用这一带地形复杂、反革命力量比较薄弱的有利条件,建立了革命根据地。短短两年,根据地迅速扩大,成为全国重要的革命根据地之一。来到这里之后,谢觉哉先后担任湘鄂西中央分局文化部副部长、湘鄂西省委政治秘书长、党校教务长等职。
在湘鄂西革命根据地,谢觉哉看到了广大人民群众对革命事业所表现出来的无限忠诚和坚强斗志。特别是一大批为翻身求解放的英雄妇女,她们冲破层层封建束缚,带领广大劳动妇女,开展土地革命,组织妇女协会,和男同志一样义无反顾地去支援革命战争。洪湖苏区的应蕙兰、张孝贵、刘桂贞等3位英雄妇女,更是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32年6月下旬,蒋介石纠集15万兵力进攻湘鄂西苏区。红军被迫离开根据地作战略转移。9月,敌人进攻洪湖苏区,谢觉哉与80多个来不及转移的外地工作人员,分乘10多只小船,躲在青草湖草丛里。在敌人发动的清湖中,谢觉哉还是不幸被捕了。被捕后,他凭借着沉着和机智,取得了敌军营长的信任,敌人并没有为难他们。3个月后,谢觉哉通过地下党组织的帮助,离开敌营,重返上海。
而留在洪湖苏区的应蕙兰、张孝贵、刘桂贞等人,在第四次反“围剿”中被俘。面对敌人的屠刀,她们宁死不屈,大义凛然,为革命事业献出了自己火红的青春。
因为当时斗争环境残酷,被俘后生死消息一时很难得以证实。谢觉哉特别关注应蕙兰被俘后的情况,从他平时的了解和观察中,他相信她“不会变节”,但又“无从获得消息”,所以身陷敌营时,谢觉哉就写诗怀念她。1934年到了中央苏区又写了这首词,直到1941年7月再次将这首词加上题记,抄在自己珍藏的日记中。
关于应蕙兰的资料,留下来的少之又少。在漫长的中国革命斗争中,像应蕙兰这样的革命者太多了。他们只有一个理想,把“活下去”的希望留给亲密的同志,把“牺牲自己”当成理所当然。他们,虽然“形影已随流水逝”,但他们却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之中,永远留在共和国的青史之中。
“你不曾真的离去,你始终在我心里。”对于谢老来说,这种对战友的思念,是刻骨铭心、历久弥新的。1945年6月,他在读了描写苏联妇女与德国法西斯进行反抗斗争的小说《虹》以后,在当天的日记上又深情地写下了这样一段话:“使我想起洪湖苏区几位农妇——张孝贵、应蕙兰、刘桂贞等同志来。她们的言语行动颇与《虹》中女子相同。她们不怕死,她们心里更没有投降字样……”